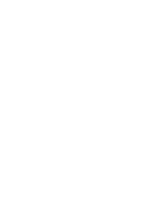去年3月我回家,看到父亲明显的消瘦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是父亲患了肿瘤?我一直关注他的血压,那时父亲的血压一直偏高在180/110mmHg以上。即便如此,父亲仍一直干着农活,我在家的那几天,他也没怎么歇着。他是个热心肠,家门口有条小水沟,一米多宽,村民出门多有不便。那天,他专门寻了一块条石,准备搭在水沟上作小桥。条石足有400多斤,我们四人用铁链拴好抬的。我与父亲抬一根杠子,或许认为我没下过重力,为了减轻我这一端的重量,他使劲地把杠子往他那边移,年过六旬的他还这样照顾年方三十几的儿子。他的关爱,我内心是有感触的。现在想来,他是带着肿瘤在挑抬啊!
1958年,父亲十一岁时,爷爷在“人民公社”的大饥荒中挑着担一头栽下去就再没起来。从此父亲便成了家里的一个小劳力,从事着农村辛苦但没多少收益的劳作。几年后,不到二十岁的他成了最壮实的劳力;大队指派他到山区修水库。抬石头是他的主要工种,报酬是工分和米饭。米饭有时省着,他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
当我七八岁时,有了对父亲的记忆。三十多岁的父亲,臂膀浑圆、黝黑,拿着打杵,挑着火砖或石灰一步一步地往山坡上的石梯稳稳当当的行进。扁担下颤抖的臂膀和肌肉是多年后在电影里看到的好莱坞影星的臂膀和肌肉。今年春节,我给父亲注射药物时,发现父亲臂膀和肌肉已经基本没有了——他的身体被病魔拖垮了。
1989年,我和弟上小学,父亲成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他到海南岛做建筑:铲沙,铲石子,扛水泥包,提震动棒。他说,他一个人当两个人干活,从不偷懒耍滑。为了多挣钱,经常是这工地刚干完就往下一个工地跑。今年春节我和父亲闲聊,我指着自己家院子说咋鼓泡了。他说那是工匠们没做仔细的缘故,震动棒没把混泥土震实在,留有气泡。他又指着对面一家的院子说,你去看他们家的地面,是几年前我用铲子一铲一铲平的,那是用了很大力气的,这么多年了没一处鼓泡的。父亲言语不多,只干不说。手艺人拿出手艺才是正道。1999年,我毕业一年多了没有工作便也到了海口,那时弟弟还在医学校读书。在简陋的工棚里,他买了两瓶啤酒,我和父亲迎着海风喝着------或许,他的头发从那时开始变白。两个儿子考中专,读医学,有分配,本应该是他的骄傲,但事与愿违。直到我和弟都结婚了,父亲才没出去下苦力。他没过多指责我兄弟俩,但也有无耐的心酸,记得他曾叹过:“你俩还赶不上没上过学的娃?”他是指工作和挣钱。那时年少的我们,谁会了解高分的中专与高中后上名牌大学的巨大差距呢?
去年3月,父亲的病情我虽有过怀疑,却没陪他去大医院做全面体检。他曾说过他右胁疼,我问他咳嗽不?他说咳嗽好多天了,我大意地以为是胸痛咳嗽,就让他买了消炎药吃。在家的几天里,顾着自己的玩,忽略了父亲的病。那时早发现早诊断,或许父亲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我返回拉萨几个月后,父亲因“腹泻,双脚水肿半月”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原发性肝癌晚期。我赶紧回家陪父亲在县医院做了介入治疗,后到西南医院开了一种叫“替吉奥”的化疗药。
再回想三月份的细节,我深深地自责,是我忽略了父亲,是我远离家乡未能照顾父亲周全。从西南医院回到老家,我陪他打川牌,给他煎中药。期间父亲的病情似乎有所减轻,腹水减少,双脚水肿也减轻了,饮食也大有改善,他自认为度过了这一道坎。今年春节,他还亲自做了一两桌饭菜,招待儿孙辈。下午他经常在太阳下和老年朋友们打川牌。但我心里明白,那是介入治疗后的短暂好转,他肝内的肿瘤仍在顽固地生长,最终会夺去父亲的生命。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电话里说他的病情,他饮食大减,喝水就胀痛,一直腹泻,疼痛加剧。我知道,父亲的病情在恶化,只能给予营养支持和镇痛治疗。父亲只是中途有几次短暂住院,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休养。他生病期间,亲朋好友都有看望过他,他每天仍坚持转悠在熟悉的村庄道路上。相比其他肝癌患者,他多活了几个月,少了些许痛楚,这就是我极大的欣慰。父亲在去年十月份就为自己置办好了棺材,他一直在生的希望和死的担忧中明朗和忧愁。或许病情好转的那几个月是他最美好的日子,因为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享受着人世间的美好,但那是短暂的,其后是更加严重的病痛。最后的日子,他迷上了所谓的“平安”教,还让我们都去信奉,去跪拜,他说只有那样他的病才会有好转。父亲在病痛中一直很坚强,疼痛时都紧咬着牙关,不大喊大叫。他在电话里讲:“我再多活几年,不能为你们种粮食,为你们种些菜蔬也好啊!”听后,我不禁潸然泪下。
爸,我何尝不想让您多活些年头?但我无能,作为医生的我的无能,作为儿子的我的无能。我能做的,只有对您的感恩和深深的自责。
父亲于2013年6月13日与世长辞。此文谨献给纪念我慈祥的、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及天下所有的儿女。
了两瓶啤酒,我和父亲迎着海风喝着------或许,他的头发从那时开始变白。两个儿子考中专,读医学,有分配,本应该是他的骄傲,但事与愿违。直到我和弟都结婚了,父亲才没出去下苦力。他没过多指责我们兄弟俩,但也有无奈的心酸,记得他曾叹过:“你俩还赶不上没上过学的娃?”他是指工作和挣钱。那时年少的我们,谁会了解高分的中专与高中后上名牌大学的巨大差距呢?
去年3月,父亲的病情我虽有过怀疑,却没陪他去大医院做全面体检。他曾说过他右肋疼,我问他咳嗽不?他说咳嗽好多天了,我大意地以为是胸痛咳嗽,就让他买了消炎药吃。在家的几天里,顾着自己的玩,忽略了父亲的病。那时早发现早诊断,或许父亲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我返回拉萨几个月后,父亲因“腹泻,双脚水肿半月”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原发性肝癌晚期。我赶紧回家陪父亲在县医院做了介入治疗,后到西南医院开了一种叫“替吉奥”的化疗药。
再回想三月份的细节,我深深地自责,是我忽略了父亲,是我远离家乡未能照顾父亲周全。从西南医院回到老家,我陪他打川牌,给他煎中药。期间父亲的病情似乎有所减轻,腹水减少,双脚水肿也减轻了,饮食也大有改善,他自认为度过了这一道坎。今年春节,他还亲自做了一两桌饭菜,招待儿孙辈。下午他经常在太阳下和老年朋友们打川牌。但我心里明白,那是介入治疗后的短暂好转,他肝内的肿瘤仍在顽固地生长,最终会夺去父亲的生命有一段时间,父亲在电话里说他的病情,他饮食大减,喝水就胀痛,一直腹泻,疼痛加剧。我知道,父亲的病情在恶化,只能给予营养支持和镇痛治疗。父亲只是中途有几次短暂住院,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休养。他生病期间,亲朋好友都有看望过他,他每天仍坚持转悠在熟悉的村庄道路上。相比其他肝癌患者,他多活了几个月,少了些许痛楚,这就是我极大的欣慰。父亲在去年十月份就为自己置办好了棺材,他一直在生的希望和死的担忧中明朗和忧愁。或许病情好转的那几个月是他最美好的日子,因为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享受着人世间的美好,但那是短暂的,其后是更加严重的病痛。最后的日子,他迷上了所谓的“平安”教,还让我们都去信奉,去跪拜,他说只有那样他的病才会有好转。父亲在病痛中一直很坚强,疼痛时都紧咬着牙关,不大喊大叫。他在电话里讲:“我再多活几年,不能为你们种粮食,为你们种些菜蔬也好啊!”听后,我不禁潸然泪下。
爸,我何尝不想让您多活些年头?但我无能,作为医生的我的无能,作为儿子的我的无能。我能做的,只有对您的感恩和深深的自责。
父亲于2013年6月13日与世长辞。此文谨献给我慈祥的、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及天下所有的儿女。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