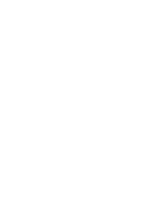一大早,就被那群反穿墨脱的青年男女给吵醒了,于是躺在床上听着他们来回走动在走廊上、慌乱整理行李、到楼下洗漱吃早饭,回忆着我们前几天出发前一样激动的心情。最后只能远远听见这些年轻、激越的脚步声消失在山口路那边。随后就是边境格外深寂的空气,被雨水打着四处飘荡。
睡不着后,就下床走出门外来到楼下那块荒地,看看我们昨晚烘在炉边的衣服、鞋子有没有干,但悲催的是鞋子依旧透湿透湿的,我决定买下脚上这双拖鞋,坚决不愿穿湿鞋上路了。
洗漱完后,正在那里整理洗过的衣服的时候,不经意瞧见杨洲虎站在楼上一脸灿笑望着我,见我已经看到他就挥了挥手,于是刚好叫他把房间里我那把木梳扔了下来。
陆续地,他们都一个接一个起了床,我也一个劲催着他们想尽早赶到墨脱,一睹它的真容。
早餐是一大碗鸡蛋面,我夹了好多给新疆的大哥,其实过蚂蝗区后,只要一吃东西真的不由自主就会有反胃的感觉,不逼着自己真是什么也吃不下。但走在路上,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和水。不得不吃!
饭后,我们决定搭车到墨脱县城,他们俩是因为公路已完全没有徒步的意义,而我是不忍再见到C拖着他那只疼痛的腿行路了。车是旅舍老板自家的,一人一百,而那辆车真是濒临报废的。但没办法,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它合适的车,除了我们四个,还有两位当兵的大哥。

我们就这样挤在那辆破旧不堪的皮卡车里在泥泞不堪的马路上颠颠荡荡向墨脱驶进了,一路上,那位四川的师傅颇以为荣地向我们宣讲他十多年的风流史,我实在气不过就跟他说其实我是他老婆花钱雇的私人侦探,专门来录音找证据的,没想到我一脸的逼真竟然还短时内吓倒了他,这些心里一辈子藏着鬼的男人,不说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墨脱。对,是墨脱,我一点惊喜也没有,因为眼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乱糟糟、飞尘遍街的刚刚开发的小城市。远远不是我们想象中、憧憬中那个世外桃源、天上仙境的墨脱。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在这里停留一夜,毕竟这是我日夜苦盼五年的地方。C自当是留下来陪我,而他们两位大哥却打算继续徒步搭车到云南丽江。于是,就在墨脱的一个邮局门口我们分道扬镳,我很喜欢他们,今生不知还能有再会之时?
分手后,我和C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来,虽说墨脱让我大失所望,但这一路走来的旖旎风景还有那种抵达梦想之地的灼热心情还是没让我陷入沮丧的情绪。放好行李后,我们就找了一家餐馆吃饭,饭毕,休息半个小时后,就拉着他到墨脱城外去走了走,至少城外的自然风光、悠远曲奇的雅江和那些栖身绿野青山中的村寨还是能够隐隐显现昔日那个莲花之城的影子。
这样的幸福今生是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与一个人这样无忧地走在一座边境之城,我对C说,很老很老的时候,回想起我们今天这样走在遥远的西域边境,也会是一件异常珍贵的温暖记忆。
中途回到宾馆又休息了四十分钟,我继续吵着他出来走,黄昏已近,大片大片的荒田里传来一种古怪的声响,C一听就说那是青蛙的叫声,可我就是不相信,猜想那一定是更神秘、更特别的一种声音,譬如是这个门巴、珞巴族聚集地特有的檐铃声。结果他拦着我们后面放学路上的几个女学生问了问,回答也是青蛙。但我还是不相信,回到宾馆趴在窗台上继续听着房后一大片稻田地里那种古怪的发声,遐想非非。
就这么,伴着这神秘、古怪的声音,入了墨脱的夜,从背崩到墨脱这一片区仿佛是没有日月星辰的,有的只是无边无际、袅袅绕绕的云雾,山边浮着、路灯上浮着、屋顶浮着、街角浮着,连人的身边似乎也微微浮着这些灵性仙动的雾气云氤。
C躺在床上看新闻,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时间静谧,仿佛一下子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不用在梦想再闯荡什么,我也不必流浪在一个又一个梦境,就这么从时间的镜子一眼望穿到我们年老的模样、今生的结局。

第十一天
不到五点,就忽然梦醒,梦的什么,醒来的刹那就忘逝得干干净净,总之一定是梦见什么惊醒的。C还睡得很熟,我悄悄下床走到窗边拉开帘子听着、看着外面夜晨交替之际琉璃珠子一样的天色夜景。于是忍不住偷偷开门跑了出去,想着也许趁着这样的时光出去漫游说不定能遇见意想不到的墨脱,始终不甘心,没看到心中那座隐莲之城的半点光影。
一走出宾馆的大门,寒气凌然,直直的街道上没有了白日的人影飞尘,昏黄的路灯默默照着深夜的墨脱,浓厚的云雾透析在这昏黄的光亮中染开一圈圈奇妙的水晕,沿着这被云雾加冕般亮着的路灯光我悠悠走着,一直走到白日和他一起逛过的那些路边田畔,膏一样的夜涂抹在天地间,除了那些无止境无时间漂流的云雾,什么也看不见,但还是来来回回像一片夜间云雾漫游在这些路灯下。
天,徐徐地亮了,有个看不清面容的男子过来和我搭讪的时候,我一气跑回了宾馆,开门的声响惊醒了熟睡中的C,他微微抬起身见我像幽灵一样溜进门来,吓了一大跳,认清是我就惊诧地问这是去了哪里?我告诉他只是到外面走了走,他再次无言以对地躺了下去。
大概八点半左右,我们从宾馆出发向另一条公路路线返回拉萨,走出检查站后幸运地搭上一辆警车,这一路我们都将徒步加搭车回拉萨。今天的目的地是波密,也比较顺利,两辆车就在下午五点半的时候搭到了波密。一直送我们到终点是西藏农牧学院一位研究野草莓的教授包的越野车,一路上停停开开很多次,因为那位教授正在沿途采集野草莓的标本。
到波密后,再搭不到车前行,就住在了悠游道国际青年旅社,在一家川味店吃了不错的肉丝面后回到住处,不多久,益西竟然也到了波密,听说我在悠游道,就过来同住了,还能再次与她重逢真的很开心,脸上的伤多已结痂,她说,小雪、左右都出来了,随后,就收到左右发来短信说是在波密附近的河边扎帐篷住下了。

陪她出去吃饭后,我们沿着河边喊着左右的名字想看看是否能找到她,但是没能如愿。只好回到旅舍,C这位大少爷又有点感冒,已经上床躺着了,我急急慌慌跑到老板那儿看有没有什么感冒药,没的话就得到街上药店去买。老板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叫我找找看看,翻来翻去,找到一包板蓝根和半袋VC银翘片,感激地到厨房要了碗冲上开水给他喝了下去,药后,效果还不错,没多久就下床去买了几罐啤酒喝起来。可能因为益西受伤不能沾酒,那晚我也没喝下多少,C喝完两罐就去睡了,我和益西坐在院子里的阳伞下再次促膝畅谈起来,望着没有星光月色的夜空,益西给我讲起她半生的传奇,这故事我说过要留着单独写给大家。
益西讲完她的故事,给我放起了赵鹏的那首《船歌》,只是听见那富有意境的旋律,就骤然被这首歌深深打动了,雨,忽然也痴心的下了起来,残残零零地听着一两句歌词,眼睛湿了、心也湿了,不知是为了她的故事、触怀的歌曲、还是这场忽然而至的凄清夜雨?益西,从小就是一个受伤的、遗落了某个珍贵东西的孩子,长大后,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救赎自己的心情还有寻觅那件遗矢的不知为何物的东西。
有时候,真不知道那种多年前心灵缺失的一部分是成全了我们某种对自我、对人生的执着寻觅与追逐呢?还是真的将我们从此抛入、放逐到了一生的缺憾、一生的遗落、一生不得安宁的宿命?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