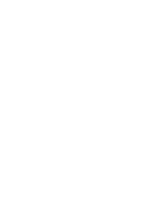我的童年是在川北的农村度过的。那些蓊郁的青山和青山间的鸟啼,纵横的阡陌和阡陌边的蛙鸣,或者还有酸酸的酢浆草和紫红的桑葚,都是我儿时的浮光掠影。它们常常穿过时光的罅隙,挟裹着纯然的快乐,将我从现实的困顿中解救出来,十年一梦,仿佛我还是那个无忧无惧的小小孩童。
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只有两个月大,刚被父亲从别人的屠刀下解救出来,滚圆的小身子抖着黑色的绒毛,睁着溜圆水润的眼睛,向我打招呼“汪汪”。我们对彼此感到好奇,我迟疑地伸手去摸它的脑袋,它温顺地伸舌舔我的掌心,丝毫没有刚被人类威胁过的恐惧,友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父亲给它取了名字叫“黑豹”,听起来威武神骏,我却执意叫它“小黑”,叫起来的时候柔软而亲昵。那一年,从油菜花的金黄到梨枝的倾斜,小黑撒着欢儿地跟在穿白裙的小女孩身后,追逐着晨光里的蜉蝣,暮色下的绿头蜻蜓,和乘着清风的蒲公英的种子,从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狗长成了像它名字一样神气的成年犬。
长大后的小黑四肢健壮,皮毛纯黑油亮,双眼有神,两只尖尖的耳朵像狼一样警觉地树立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帅小伙”,这一点从它出门巡逻时身后益发壮大的跟班儿队伍得以窥见。它像是这个小小世界的王者,每日骄傲地昂着头,带着它的“亲卫队”,巡视于田边屋后。
它是合格的“亲卫队长”。它有敏锐的听觉,总是在半里地外就能准确区分陌生人或是熟人的脚步声,然后决定是咆哮着发出警告还是摇着尾巴上去撒欢儿。那时侯,家里养着大群的麻鸭,落日西沉的时候总有几只流连田野,不愿归家。它会跑过去,赶着它们全数回到竹篱围成的圈里。或者是到了秋天,地里有各种成熟的瓜果,它便不再回到我们在屋檐下为它搭的窝里睡觉,只在田间找一处茂密的草丛,夙兴夜寐,防着过路人贪婪的手。
它是优秀的猎手。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它兴奋的叫声吵醒,揉着眼睛开了门,看到地上躺着一只皮毛雪白的小狐狸,脖子上有几个新鲜的血洞。父亲说,这是它带着它的“亲卫队”围捕来的猎物,后来,那狐狸皮还卖了不少钱。此后,便不断有动物被它拖回家,我们全家时不时就会吃上一顿野味。这些本是它的胜利果实,然而,它从不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
它是亲密的伙伴和家人。它在外面总是威风凛凛的样子,在家里时却还像小时侯那样爱撒娇。在我们忽视它的时候,它会用头蹭着我们的裤腿儿,直到我们注意到它,才抬起头睁着圆圆的眼睛和我们对视,眼里有纯粹的信任和亲近。或者在父亲的指示下叼各种东西,乐此不疲,雀跃地在家里跑来跑去。家人曾告诫过我,狗狗吃东西的时候不能抢夺它的食物,否则就算是主人也有可能被误伤。然而我从小是顽劣的孩子,怎么甘心不去试探这样的底线。我和它嬉戏,把它的肉骨头从它的嘴边踢走,反复4、5次后,它终于恼了,低低地咆哮一声后便呲牙朝我裸露的大脚趾咬下,我一时间惊骇地忘了动弹,心中后悔不迭。然而,它的尖牙一触及我的皮肤便停止了攻击,只是用舌头舔了我一下,便抬头看我,眼里仿佛有委屈的光。现在想起来,我如此的肆无忌惮,大概也是自恃亲密,想要挥霍一下它对我的纵容罢。

我当然知道小黑没有人类的寿命长,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它便要成为我的回忆。我11岁,尚未经历过亲近之人永离的伤悲,对生命不够敬畏,对死亡稍嫌轻慢,想不到它会以这样阴险的姿态在生活的路口张网以待。
那时,小黑成为我们家一份子已经5年,有一天出去后便没有回来,第二天周围邻居养的鸡就被偷光。这实在太过巧合,我们不得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它失踪背后的阴谋。等我们找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在回家路上一条干涸的水沟里“睡了”很久,不远处有一撮拌了老鼠药的红薯粒。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小黑是个奇怪的家伙,它摒弃了喜食肉食的天性,却对红薯情有独钟。鉴于此,我们家从不在自家的田地里放老鼠药(那时侯的老鼠药都是用红薯拌的),而它也不会吃别人丢给它的食物。那我家地里的老鼠药是哪来的呢?这答案简直昭然若揭……
我慢慢攥紧双手,仍然无法发泄我左右奔突的愤怒和伤心,只好在臆想里将那卑劣的偷鸡贼用我所知最残酷的刑罚狠狠折磨。我被自己隐秘的暴戾惊吓到,却无法停止这种悲愤,直到它寻找到出口,流成滂沱的眼泪……
有时候,我会去看它,那个小小的土堆里埋着我亲爱的小伙伴小黑。从此以后,它要独自沉眠在这冰冷的土里,在这片它曾自由奔跑过的广袤的原野上再也没有它的身影,而它终将变成植物的养分,看那小土堆上蓬勃的绿意,它已经以另一种生命形态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
它与我失散在我十一岁的那个夏天,死于人类因贪婪而滋生的阴谋。它是我的小伙伴——小黑。我时常怀念它,如同怀念我不可追忆的童年时光。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