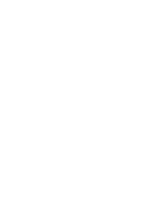今年清明,我在拉萨拜了佛祖,未能回家乡祭奠亡人。
自外祖父见背,十数易春秋,伤痛不曾减。多少次梦里,外祖父犹在小路屡屡回头望我。梦里我心焦,恐他又走,泪咽无声。
外祖父肺癌晚期,临终前几月,总是要往医院里跑。母亲劝他住院,外祖父绝不肯。我猜他是担心不能回家。那个夏天正是非典,家家都在消毒,学校也放了假。每次母亲去医院,我便要闹着跟去,可家人不允。我在家里便害怕,怕外祖父回不来,总坐在楼道门口全身颤抖。直到看见外祖父回来,恐伤他意,我方强把眼泪复收。后来,外祖父知我害怕,他便和我讲,每次去医院时,他回头望望家里的窗,便知我在,他心是安的。这么多年,我每每想起外祖父离家前望我,心是要碎了。
今夜若是梦,久应醒矣。
幼时,我有些痴。喜欢了一株花,日日去阳台看,数它的枝叶。记录它每天有几只蝴蝶来做客,看它是否明日还要开花。那株花有特别的味道,我相信有仙子住在里面。外祖父知道所有我和那株花的故事。母亲每日上班,她并不知道那株花的秘密,只有外祖父听我讲,听我告诉他今天又和这株花说了几回话。

一日午后暴雨,它伤了根叶,母亲随手把花扔进垃圾桶。我看见它时,残破的花枝和果皮破布躺在一起,仿若一个哀怨的尸体。仙子一定也死在花里。我受了极大的惊吓,窒息般的尖叫起来。外祖父方睡午觉,闻声奔来,拖鞋都不及穿。我蹲在墙角,似受伤的小兽。母亲只呆在一边。我掉进了自己的深井里,怎么都爬不出来。突然有一双手,将我稳稳的抱起。我在外祖父的怀里。他慢慢摇,轻轻的拍,整个宇宙都温柔起来。我渐渐从深井看出来,有暖意,有阳光。外祖父已抱我到院子里,他抱着我在小院里踱步,我不再尖叫,在外祖父的怀里轻声抽泣。外祖父带我看小院里的花们,牵牛花,火红的大杜鹃,金黄的向日葵,还有小小的朝天椒。我又看见了仙子,它坐在一株无花果里。我是这样又怪又倔的一个小东西,只有外祖父觉得我很好。他反复告诉我,我很特别,我很完美,我很重要。
我上一年级时只有五岁,上了半年,就被老师送回家里。老师和母亲讲,这个小孩很怪,不正常。我会自己讲话,那时我很矮,没有小朋友肯和我玩,我就发脾气,打了小朋友,也打了自己的脑袋。老师讲,哎呀这个小孩好奇怪的。她让母亲把我送去特殊学校。外祖父大怒,母亲说,那天外祖父把老师从家里赶走了。
大约是我缀学一个月后,母亲用嫁妆给我买了一架钢琴。外祖父每月从退休工资里拿出四百块钱,送我学钢琴课,带我去北体听演奏会。风和日丽时,外祖父便骑着二八大自行车,骑很久,带我去北塘海边看渔船。渔民站在船头,捞出一筐筐的泥鳅和小螃蟹。有时外祖父会买回来几只,让我用小竹筐提着,放回海里。有时,我们也不看渔船,就只看着夕阳沉沉入海。
快到家时,天总是黑的。外祖父骑着自行车,吱呦吱呦,我在后座摇摇欲睡。外祖父在我的座椅上缠了艾条,没有蚊虫扰。夏日的晚上,外祖父给做我凉拌西瓜皮和鸡蛋羹。两个鸡蛋打碎,倒进一点水,一点点盐,然后在小锅里倒进水,连碗放在锅里一起蒸。不一会儿,碗里的鸡蛋便凝固了,蓬松松的,外祖父再倒上一点香油。至今,有时人生郁结挫折,我就给自己做一晚鸡蛋羹,热气腾腾的香气扑在脸上,冰也是化了,眼泪滴进碗里,心也就活了。
那年秋天,我长高了。外祖父给我转了学,去另外一所小学上了二年级。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自己和自己讲话这件事。其实我都记得。是因为没有小朋友和我玩,我又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孤单,所以就假装在和一个别人都看不见的朋友讲话。我以为大人没有朋友时都会这样。外祖父从来没有问过我,我猜他都知道,就像他知道我和那株花的故事。
我出世时早产,母亲身体亦弱,住院不能行。我小命垂危,总是看着游气一丝。刚出满月就得了脑膜炎。惊厥嗜睡,当时父亲家的爷爷喜男孩,并不理会我。外祖父果断,独自抱我连夜坐火车赶回北京医院。幸得康复。大约我天生气血不足,长到三个月尚满月婴儿一般,外祖父怜子心切,听医生说喝羊奶有好处。那时正逢深冬,外祖父每日天不亮就骑车去郊区一家农庄,打满两个军用水壶的羊奶,捂在胸前棉袄里带回家,够我喝一天一晚。第二天他再去。有一次雪天路滑,外祖父摔了跟头,伤了左胳膊,车链也断了。外祖父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把车推回家,家人惊问,他说,幸儿的羊奶不曾摔。
多亏外祖父的羊奶,我尚有今天。
我有一对儿银镯,很小,是小孩三岁时要带的。外祖父给我的。家中有三个哥哥,但外祖父给了我。这对儿镯子,是亲外祖母的,是文革后她从藏区甘孜带出来的东西中,仅剩的几个。还有一对儿金耳环,他给了母亲。我结婚那年,母亲给了我。母亲年幼丧母,我从未见过亲外祖母。家中有她的照片。我上大学时,偶然翻出了一张她和外祖父的照片,他们穿着衬衣微笑,仿佛岁月安稳,山远水长。那日,我惊愕发现,我竟和外祖母如此相像,我想,外祖父看我时,一定看到了外祖母的影子。
外祖父生病时,我问过外祖父,如果有一天他死掉了怎么办。他说,那一天到了,不要很难过。安安静静。外祖父说,人都要离开的,走了才能再开始。我眼泪掉不停,外祖父大笑,他说我像海军后勤院里的那个松鼠,抓住一个果果就不肯撒手。外祖父说,就像那株花,它死了,仙子还可以飞进另一株花里。人一生这么长,总会有另一株花等着我找它。外祖父说,等我长大后,无论遇到再大的悲哀,要我保证用力呼吸,不管再难,只要呼吸,用力的呼吸。

三个月后,外祖父走了。可我不在。外祖父临终前,一直在找我。母亲和兄妹们给外祖父穿衣时,外祖父一直在找我,不停在念念。我怎么不在。那天,我记不得了。记不得到底多少人来吊唁。记不得哥哥们在干什么。记不得门口有多少鲜花。我痛的几乎失去知觉。尖叫哭喊。可我一直在呼吸,我觉得快要窒息时,我就用力呼吸。我尖叫颤抖时,我就用力呼吸。外祖父,他要我用力呼吸。我想他会欣慰。
那年,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老人。
每年过生日,外祖父都会送我一本书。我十二岁那年,他送了我一本《周易》,其中有一个乾卦:上九:亢龙有悔。我不懂,便拿去问他。外祖父说,做事需有盈亏,不可太满。太贵,太高,则盈不可久矣。他要我日后做人不可太满,不可太过。他要我平淡,方能长远。
外祖父一生清洁,为人公正。不争,不胜。外祖母病逝后,外祖父独自带大五个儿女。不焦,不燥。而后,大女儿因故盛年去逝,家中乱做一团。那时我三岁。外祖父白发送黑发。在大姨的葬礼上,外祖父依旧站的挺直,默默地照料大女儿的身后事,甚至出殡时临时从小卖店赊走的几盒柴火,他都一一亲自上门道谢、归还。周易中还有一卦:动乎险中,大亨贞。每到家中有难时,外祖父亦是如此。平静而厚重。如同一座大山,端端地守住在风雨中这飘摇的一家人。
上到小学六年级时,我要小升初。母亲督促我补习,那时还上了书法课,钢琴课,奥数班。我日日焦躁。那时外祖父又查出肺癌晚期。每天吃早饭时,我就要偷偷掉眼泪。那时父亲那边的爷爷也查出了血癌。母亲压力自然大,为了使老人能得到最好的医疗。她和父亲买了一辆出租车,白天租出去给别人,晚上下班后,她就和父亲轮流跑出租。全家人都只和外祖父说是肺炎。
有一日放学,我见外祖父在学校门口。他微微笑,摆手招我过来,他带了我去桥头看相声。人流熙攘,外祖父把我扛在肩头。我抬头望,夕阳,日色如金。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问外祖父,为什么母亲们要和他撒谎。他说,有时大人们也会害怕,大人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时,也要有地方躲避一下。所以母亲们会撒谎,我想是她们怕了。外祖父,他一直都知道,他从来都没有害怕。
母亲为了延长老父的寿命,天南地北求医问药。回家以后,她就会熬出各种药,外祖父从来不问。小女儿端来的药,他就一口喝下去。母亲们带他去医院,他就顺从的躺在病床上。在我的记忆中,外祖父肺癌晚期的那三年,母亲一直都像一只紧张的鸟,四处慌张奔走。而外祖父总是端然的晒着床头的阳光。我想,母亲害怕了,她害怕会失去父亲。而我比她还要害怕。
外祖父和我讲,母亲太要强。他说,有时人需要认输,需要顺从命运。外祖父大约早已听了天命,而他吃下的每一份药,都是心疼儿女们而已。
后来念及,外祖父离逝时,我与母亲们本不应痛哭。他走时是安然命终,子孙们的哭喊,岂不是扰了佛号颂动,反使外祖父不得清净。又想外祖父向来心水澄净,视净土如归,他听见我们的昏乱,必然也只是微笑,是不曾误了的。可是最终还是误了。
入少先队员时,外祖父问过我,将来长大想要做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干,想去种花,晒太阳,养小狗。他大喜。他说,长安少年无远图,这是极好的事情。
我想外祖父不仅修襌道,亦精于世理。
文革时,外祖父关了隔离所。与外祖父相与的昔日好友,同党,除了也落此下场的,其他的便是疏远了去。家中有五个幼儿,外祖母胆小,言语不通,又绝不肯断了关系。每次去合作社领东西时,就不停的说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万岁。这是外祖父教给她的。别人说外祖父不好,她便不依,抱着小女儿大吵大哭。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然外祖母回护之情,便是天地皆正了。每次外祖母带着幼子们看望丈夫,外祖父只能要她们努力加餐饭。后来,我读了东汉诗人的一首诗,其中一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再想起这一节,我大拗。于他们,人间福祸劫难种种皆真,甚至不必誓盟。
自幼时,外祖父便教导我要修法修身。可惜我听得,却从不曾领会。他教我人世庄严,不可亵玩。就好似一朵花,炒菜的锅,都自有它的道理。不可拿来当玩物。小时候,总有大人买了布娃娃给我。一抱娃娃起来,它便会眨着大眼睛。我爱极,便要大人多多买来给我。外祖父不喜。他觉小孩子不应此心太重。
不止是于物,外祖父对人世更是如此。不可我贪,不可尽求。吃饭要有礼。若有一日做贫贱之身,食前也需净手。坐要端,走路要正。外祖父说,人世最不可负的就是此心。若欲念太多,必然会失真心。外祖父向来不当我是小孩,他觉得小孩子才是担着大事,故一言一行更要稳。
如今,我一无所成。但我想外祖父必然是喜欢的。因我始终看重此心。成年后,总能看着世间百态。我从未因贪图荣华走错一步。每行一步,只要走的遂心,走的清明。偶尔走快了,我就停下看看。自幼外祖父就教给我,此心平稳,自能避险。有时看身边的人,忙碌无处,竟不知他们的此心还剩多少。我便觉满足。外祖父说,人间并不清平,天地大动,泥沙,枯草有时浑浊在一起。而此心在,就是完整,就是真人。
幼时外祖父总是逗我,讲我是如来之身,不受劫毁。多年后,我一次大病。手术后,医生讲我是癌晚期。我父母几乎被唬去性命。父母害怕了,也骗我无事。可我总是识得,可心下明白,总觉自己不至如此,想着应该是不碍的。然也亦想过,若当真有此劫,我是要从楼上跳下去的,绝不肯拖累了父母。手术后七夜,我夜夜梦见外祖父。他在路尽头望我。有次梦里,外祖父蹙着眉头,眼里有泪。这一梦让我心大痛,我拼命摆着手,喊着我不妨事不妨事的。那些天,母亲每晚坐在病床下打坐。后来她和我讲,那时她的脑海里总有三支佛灯,有一个在逆时针旋转的钟表,那些夜晚,她不停用意念转那个钟表,第七晚,那个钟表停止倒退,终于顺时针在走了。
第八日,医生说我平安大吉。半月后我便出院了。我并不辨此中玄机。只是想起外祖父曾说过的一句话:常人常为境转,强者而能转境。我定然还是有几分福份与根基。
成年后,每每有难,我便总能梦见外祖父。这使我不安。开始担心,外祖父莫非惦念我,终没能走了轮回。家人去寺庙看,讲外祖父并不曾走,我大悲,他定是因我而受苦。有年冬天,我去了青海塔尔寺,从进寺门那一刻,我的腿一步沉似一步,心里哀痛沉重。行至大殿下时,我已是一步不能前。佛前一面,不禁失声掩面大哭,以至连一个长头都拜不成。有人轻轻将我扶起,有人接过我手中酥油灯。大殿冰冷,不知在殿里呆了多久,我却全身发热。
一个月后,家人为外祖父做了法事。至今两年,我再未曾梦见过他。那日我在大殿哭泣,心心念念只是他。我想他将我交回到佛前,外祖父终是安心了。
《西游记》中有一段话:孙悟空打死小妖,变做它的模样,去请九尾狐狸精,到了二层门下,闪着头往里观看,见那当中有个老妈妈。悟空见了,在二门外捂着脸,脱脱的哭起来。你道他为何哭?自然不是怕,当年他曾下九鼎油锅,炸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点儿泪。只是心想,进了门就要拜这老妖磕头。俺老孙为人做了一场好汉,只拜三人:西天佛祖,南海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他四拜。为了他一卷经,俺老孙要拜这妖。苦啊!算来只为师父受困,故使我受辱于人!
老孙只拜三人。我一生便是蒸不熟,煮不烂的石豆豆,也只拜三人:西天佛祖,生我父母,最后一拜便是外祖父,拜他于我大恩,拜他亲我育我,点我启蒙,开了我聪明,教我成人,庇我于大难大险。只拜我外祖父四拜,若有来世相逢,大恩再报。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
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甲联赛第十一轮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